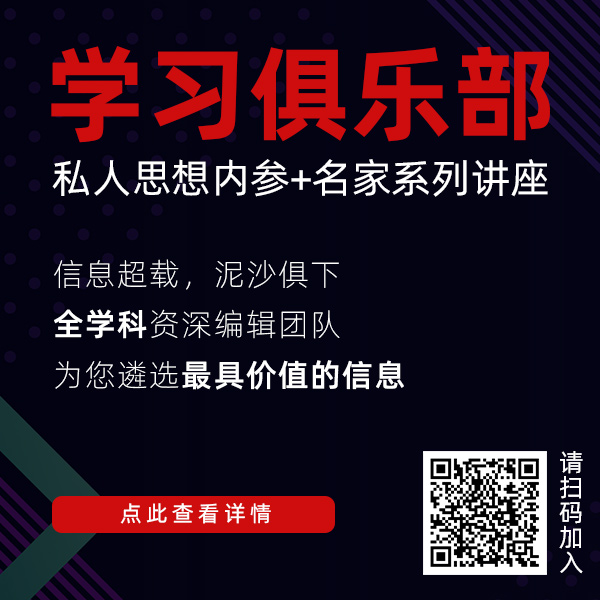王汎森: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
- 2020-08-04 01:23:45
- 来源:王汎森: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83 次 更新时间:2020-07-31 01:02:21
● 王汎森 (进入专栏)
在第一部分“传统的非传统性”中,主要是想探讨尊孔与复古这两种精神动力为何可能导出一开始完全意想不到的反传统结局来。在尊孔的部分,我举了廖平与康有为为例;在复古方面,则主要是以章太炎等国粹学派的健将为例。在第二部分中,主要是想探讨爱国的思想,为何也可能导出反传统的结果来。
一、传统的非传统性
(一)从尊孔到反传统
“西学源出中国说”是晚清很有力量的一派思潮。这派人的论调看起来极为保守,其实却潜存两种可能性:它可以成为抗拒西学的有力武器,但也可以成为要求吸收西学的有力护符。我们可以说在这一个躯壳中,事实上拥有两个灵魂,一个极保守,一个极激进。从保守的一面来说,“西学源出中国”的说法,正可以使人们进一步相信,只要能重新掌握古学的真谛,即可以克服西人的挑战。从激进的一面来说,此说无异于承认当今的西洋文明与中国的古学不但不相违背,而且是密切关联的,故吸收西学即等于是重光旧学,所以此说无异于间接承认了某些西学的正面价值。因此,在“西学源出中国说”这个看来极保守的面具里,我们竟然看到两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性。
俞樾(1821—1907)在为王仁俊(1866—1913)《格致古微》所写的序中,大力称赞这部书宣扬“西法”尽包孕于中国旧学的道理:
使人知西法之新奇可喜者,无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方今经术昌明,四部之书犁然俱在,士苟通经学古,心知其意,神而明之,则虽驾而上之不难。此可为震矜西法者告,亦可为鄙夷西法者进也。[1]
我们应该注意到前引文的最后两句——“此可为震矜西法者告,亦可为鄙夷西法者进也”——俞樾的意思是:因为西学源出中国,故不必“震矜”于西学之奇;但也正因它源出中国,与中国古学不相违逆,故也不必“鄙夷”。这段话不正为保守与激进两种可能性作了最好的展示吗?
接着我想谈清季今文家与这种思维的相似性。在开始谈廖平与康有为之前,我想先提一点,康有为为了支持他的变法改制,把孔子由一个历史文献的整理者改造成一个提倡变法的哲学家。这一来,推倒了古文经的地位,说古文经都是刘向、刘歆父子所伪造的,连带地使古文经中的内容受到根本的怀疑。除此之外,他还处处想“会通”孔子与现代的西方。
廖平、康有为与早期的梁启超在会通“孔子”与“西方”的技巧颇近于“西学源出中国说”,只是一时不易从外表觉察出来而已。他们在技术上一样是“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2](梁启超语),背后的动机都是在替当时地位逐渐动摇的孔学注入新活力,使他可以继续保持其“生民所未有之圣”的尊严。
本来,对每一个时代的人而言,某些经典是不是还有活力,端视它能否有效地关联呼应当代的境况。但“关联呼应”(correlated)时代的境况是有一定的途径与分际的,它一方面要随时注意境况,用合于那个时代的概念工具来宣扬学说,一方面要不失其本质与独特性。如果它完全不关心时代的境况而自说自话,那是一门吸引不了人的学问,但是,当传统儒学参与现代的境况时,假如解经者是从现实境况的诸问题中寻求六经的解答,六经本身也就丧失自我的本质与独特性,反过来被当代的境况所决定了。对任何时代的经学家而言,这都是一个很难掌握的分际。而廖平、康有为在替孔学注入新活力时,正好陷入这一困境中。
廖平、康有为是如何陷入自己编造的陷阱中呢?这是个相当曲折的问题。
晚清的现实境况不时在对儒学提出问题,而且大部分的问题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像先秦诸子在晚清便逐渐有由末席跻上首座的趋势。廖平必曾为这个问题感到难堪,为了特尊孔子的地位,他选择了一个特别办法来解决,主张诸子皆宗孔子。廖平说:“孔道恢宏如天如海,大而八荒之外,小而方里之间,巨细不遗。”[3]在他看来“孔道”是无所不包、巨细不遗的。转一个角度来说,“孔道”对诸子百家是不排斥的;非但不排斥,而且还有密切的源承关系。他很含蓄地说:“子家出孔圣之后,子部窃孔经之余。”[4]廖平原是想说明孔子包容一切的伟大,但却造成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就是将原先被视为异端的诸子说成是孔门的“分枝同本”、“仅如兄弟之析居”。[5]譬如墨子,他说:“墨家之宗旨,要皆圣道之支流。”[6]廖平发表这些意见的原初意图是为了“奇伟尊严孔子”[7],结果是替诸子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廖平为了增强圣人之道的绝对性,主张它包含一切,但实际的结果却是使孔子的思想中不容许有任何违反诸子学的东西,将圣人之道降低到和过去认为是“异端”、“邪说”的诸子学并存的地步。
至于西学的挑战,更是令他心焦如焚,举个例说,严复(1854—1921)从英国回来就曾上书说:“地球,周孔未尝梦见;海外,周孔未尝经营。”[8]这个质问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对晚清士大夫来说却是极为亲切、沉痛的。廖平与康有为等孔学传统的坚强拥护者面对这一类挑战时,心中的冲击必定是非常巨大的。事实上,严复的那一句话在廖平的书中便被引用而且表达了严重的关切,从廖氏的自述中可以十分清楚地发现:从某个层面来说,他之所以根据早年被自己驳得体无完肤的《周礼》撰写《地球新义》,即为了回答严复提出的问题。在晚清这一类的质问与挑战为数不少,如果孔学无法做有力的回答,那么它又有何“奇伟尊严”呢?廖、康二人便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从事代答的工作。
从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廖平、康有为替孔学回答晚清现实社会挑战的方式是很奇特的。他们毫不考虑地将自己认为对这些挑战最好的回应注入孔子的躯壳中,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为孔子装填了许多孔子自己也不认识的异质思想。
以廖平而言,他为了特尊孔子,乃将所有“经传所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帝德王道伯功”说成“皆属一人之事”。在他看来,这个说法足够回答那些把六经当成史书的考证学者所怀抱的一个看法:孔子整理六经,而六经所记大多为周公所创的制度,孔子只是一个记录之人,那么周公自然贤逾孔子。但廖平发现这还不够,不只是六经中的“帝德王道伯功”应该是属于孔子一个人的,连现今欧美各国的所有文明都应该是孔子所曾昭示过的,这样,孔子的学说不就是超越所有时空限制的伟大巨构,更有理由屹立于当前世界而无愧色吗?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他大胆地以预言的方式解释孔子学说。把握了这个前提,才能了解廖平所作《孔经哲学发微》《地球新义》《皇帝疆域图表》等几乎不可理解的释经之书真正的意涵,也才能理解这个经学家在理路上极为讲究,但内容却荒诞可笑的解经文字中,有深刻而急切的用心。上面几部书的一贯特色是把全球五大洲的发展以进化先后排列,中国居最高,其他各洲依清末民初的强盛程度排列,把它们统统纳入六经“预言”的范围中。他以预言代替历史作为儒学思想的内容,经此一举,孔子变成了有生民以来所未曾有的先知,但却也带来与他原来意图完全吊诡的结果。
从表面看来,廖氏有意压低西方各国文明的地位,但实际上是去除了中国文化与他们的隔阂,进而希望接纳他们。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居于文化发展最高阶段的中国,如果想吸收发展程度较低的西洋文化时,是丝毫不失其自尊之感的。况且夷狄(西洋各国)的文化既是圣人在六经中预言所及的,则我们今天又何必对它们感到见外?这层意思,廖氏在《皇帝疆域图表》中说得最清楚——他说“大同世界,无所谓夷也”。[9]
廖平宣称西方现代文明为孔子所预言过的,西人对中国的挑战也都是用孔子的思想作为武器,故他在为孔学注入新活力时,不只是坚持孔子知有外国,而且强调西方“但施之中国,则一切之说皆我旧教之所有”。[10]他这样的用心,是想加强孔学回应现实困局的能力,以保住孔子的尊位,故说:“自成其盛业,孔子乃得为全球之神圣,六艺乃得为宇宙之公言。”[11]用章太炎的话说,不管廖平或康有为,他们种种作为的原始意图都是欲“奇伟尊严孔子”。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个行动的副产品是将一向不理于保守派人士之口的西学吸纳入孔学内部。
从康有为的文字中可以发现,当列强瓜分中国之局将成时,他心情非常之焦急。当时他的主要关怀是如何“保教”,也就是一方面保住中国,另一方面使孔学不致成为一门过时的、没有活力的学问。而在他看来,保住中国正是保住孔教的大前提,所以大力主张变法。但他所拟的强国之道是吸收西方人之法,而用来支持其吸汲西学的理论基础是这样的:
为尊祖考彝训,而邻人之有专门之学、高异之行,合于吾祖考者,吾亦不能不节取之也。[12]
他还把当代西方政法学术等同于“三代两汉之美政”[13],故从他的逻辑来看,吸收西学即所谓“尊祖考彝训”。西学“合于吾祖考”,而当代的中国反而不是先圣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在他看来,中国先圣的理想既被“外夷近之”,则外夷“虽其先世卑贱,[中国]反为之屈矣”。[14]
他用这个论据来抵挡各方面的攻击,故当朱一新(1846—1894)斥责康氏是“阳尊孔子,阴祖耶稣”时,康有为答以“是何言欤?马舌牛头,何其相接之不伦也”。[15]当大家认为康有为是在压抑国学以兴西学时(用朱一新的话说就是“嬗宗学而兴西学”),康有为觉得他的敌人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康氏自认为是在提出一种新的孔学来抵抗西学的挑战。当时人认为他是在肆无忌惮地毁弃中国之学,他却自认是在更有力地坚守据点。
既然现代西方之政法即等于中国“三代两汉之美政”,那么如何把这些“近事新理”缘附到孔子身上呢?这是托古改制论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了使缘附的工作做起来更无忌讳,廖平、康有为把经书中的史事解为符号,像廖平便把历史上的鲁、商二国解成是“中”、“外”、“华”、“洋”的符号,而这类新解在康有为的《改制考》中更是到处可见。该书卷十二上说:
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王之所寄托……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16]
他之所以费心抹杀尧、舜、文王的史迹,就是想腾出空间,注入“民主君王”的理想。此外,他还用类似的方式把重女权(男女平权)的理想及选举的理想说成是孔子所已有[17],而且愈演愈烈,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所撰成的《中庸注》中甚至把“欧美宫室”说成是孔子旧制。其言曰:
孔子之制皆为实事,如建子为正月,白统尚白,则朝服首服皆白,今欧美各国从之。建丑,则俄罗斯回教徒从之。明堂之制三十六牖七十二户,屋制高严……则欧美宫室从之……[18]
《春秋董氏学》卷二中的“王鲁”条中亦说: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314.html
- 分享到: